- 不老诗心堪月同
- www.nhnews.com.cn 宁海新闻网 2019年06月24日 09:53:5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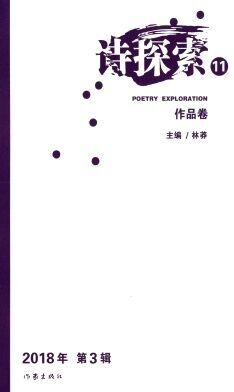
南溪生
在潘老师喜寿之年,《诗探索》重磅推出了他的30首诗作及其创作随笔《跟上队伍》。这看起来就像在一个最恰当的时候给予一位笔耕不辍的老诗人的一种致敬,也是一份特殊的厚礼。
对一个纯粹的诗人而言,没有什么比诗本身更厚重的礼物,也没有什么比诗更好的致敬方式了。
我与潘老师交集不多,偶或见面,也多是作协举行的活动上。数语寒暄,其长者之风便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认识他主要是通过他的诗歌。读其诗越多,疑惑就越深:是什么力量可以让一个人一辈子毫不厌烦地去做一件事?我想没有别的,唯有热爱。热爱才能持久,热爱才能让他的创作老而弥坚,始终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和生命张力。
作为比食指、芒克、江河都要早的诗人,潘老师的诗歌创作就是一条涓涓细流,安静,久远,从不嘈杂。而他的诗,就是生命之河中泛起的浪花,每一朵都饱含着他的情感体验,对世界的独特感知。我相信,潘老师就是那种手里攥着生命密码的人,他有通过诗的语言去解码、打开世界以及人生的能力。
潘老师的诗,多是短诗,最长的也不过数十行(诗传除外)。但诗歌的写作难就难在短而别致,短而丰富,短而有味。其味,大抵有三。
隽永之意味
这里所谓“意味”,指的是诗的蕴藉内涵。好的诗歌一定是富有意味的,蕴藉越丰越多元,越是指向各种可能,也就越值得咀嚼品鉴。
潘诗有两种比较明显的倾向,恰如诗歌本身具有的两种力量,一种向外延展,是淡雅的、清新的、活泼的。这一类诗,仿佛荷叶上滴着的晨露,晶莹透亮,会翻转,会滚动,会折射出各色光和影。譬如:
牛蹄窝窝里盛着蛙声/牛蹄窝窝里盛着犁铧闪亮的语言/牛蹄窝窝里盛着/路边野花涌来的山歌/牛蹄窝窝里/盛着桃花鲜红的羞涩……鸭子叼着/半截发绿的活蹦活跳的小溪/四处乱跑(《春二三月》)
譬如:“鸟儿的翅膀载着/很大很厚的冬天飞去……老柳树一手托着鸟巢/一手托着带潮气的太阳”(《春天像开场锣鼓露出脸儿》)
即便是写夜色:“几点星光/粘在凹凸的夜/半片残月/坠入我泥土般的梦/溪水潺潺/有人在自己身上寻找星星”(《今夜像只陶罐》),也如梦似幻。
海德格尔曾给诗人定义,谓诗人是神圣的命名者,需要具备一种与万物沟通的能力,通晓自然的语言。而读潘老师的诗让你感觉,他不仅与万物沟通,甚至能召唤万物,如同一个手握魔杖的魔法师。在他的笔下,就算是“大青石”这样的“死物”也有活的气息,“低矮的冬天压着大青石/大青石上粘着刚熄灭的火/大青石上有条细线般的裂缝”,这裂缝断然不是简单的裂痕,至少让人想到某种“生命的裂痕”。
另一种则是向内生长,是曲折的,含蓄的,委婉的,甚至带有魔幻的荒诞的神秘的超现实的色彩。在这一类诗里,他非常虔诚地为细小凡俗的事物做经验提纯,凭借对生活独特深刻的洞察和下意识的直感神助,揭示常人习焉不察的细节,为读者呈现经验的多层次存在。譬如:
树走动了几步/又回到原来的位置/我放好双脚/用一颗没有颜色的心脏行走/双手扶着弯曲的微风/蟋蟀/用两根触须捅开夜色的一个窟窿/树,抢先涌了出去(《夜色》)
在这里,人和物随意置换,诗歌提供的场景就像一个魔法世界。弱如蟋蟀也有强大的力量,能捅开夜的窟窿,树具有漫天生长的神力,能涌去天空。而没有颜色的心脏,弯曲的微风,显然都是一种隐喻。心脏代替了双脚,且没有颜色也就缺失了活力,且所能扶持的只能是微风,还是弯曲的,可见这行走之艰难,步履之沉重。这显然暗合着某种人生的历程,或心路历程。其中,也可见诗人对自身存在的世界保持着距离性观照。在这一类诗里,现实的经验退后,诗歌的面罩拉开。
再譬如:牛绕了半个村子/沒去闻闻/麦苗碧绿的诱惑/找到了一幢房子/大口大口地吞吃钢筋/吞吃水泥/吞吃砖块/吞吃瓦片/夜的边缘/塌方(《牛的行动》)
这就很有些神奇了。牛对麦苗失去了兴趣,反而对钢筋水泥砖块大快朵颐。可见,诗人笔下的牛已不是寻常的牛,是象征意义上的牛。它的吞吃导致的结果是“夜的边缘塌方”,塌方之处即是曙光漏进来的地方。牛,某种程度上是引来黎明的先驱。
再如他写水中的芦苇,“湿漉漉的梦中/一枝挺拔的芦苇将枝叶伸进太阳”,这个芦苇不仅是倔强的,甚至带着某种神性的光辉。它不屈服于波浪,一次次被淹没后又一次次站起来,伸进太阳但不是飞蛾投火,而是自我价值的追求,太阳成了一种理想的“彼岸”。
在诗人的笔下,很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事物都被赋予了一种倔强的个性。比如一条藤蔓,“触须/紧紧抓住根部的泥土/蓬蓬勃勃地往前爬”,一个卑微的生命,不遗余力为生存而努力的形象跃然而出。
独特之趣味
这里所谓趣味,也有两个层面。
其一,是童趣,天真烂漫之趣。这是潘诗的一个鲜明特性。乍一看,有儿童诗的味道,但仔细品味,无论从形态、手法、意境的营造、深邃的思想上显然不是一般儿童诗可比拟的。只是在奇特瑰丽的想象、纯真稚朴的思想方面,二者多有共通之处。
诗人者,赤子之心。在诗中,诗人把省察万物的视角放得很低,总是以齐物的视角平视这个世界,并像一个孩童一样对万物都充满着好奇心。一株植物,一个小动物,一个极其普通甚或卑微的人,都在他的笔下生发出或静默或活泼的美好。在他的眼里,狗的吠声能够“把山村抬到星星的上面”(《山村的夜》),见群鸟飞翔则联想到他们的“翅膀压低了黄昏”(《独山》),怪老天爷“坐得太高了/你能否坐在村西的山冈上”(《老天爷你坐得太高了》)。看着冬天十二月的天空,生发出这样的疑问:“七个窟窿八个窟窿/老枣树伸出好多的手/在天空上写些什么?”完全是一种童稚之气,童稚的眼光,童稚的心理。他甚至于“蹲下,掰开一块泥土/看见众多蚯蚓翻耕着自己命运的声音”,对于小如蚯蚓也给予足够的生命尊重,这就完全是不掺任何杂质的纯贞之心了。
在《鸭子,不能把我的云彩叼去》这首诗里,这种童趣就更足了:飘过来了,飘过来了/云彩:红的、黄的、蓝的、白的/池塘/清清的水洗着云彩……忽然,对面来了一群鸭子/我急忙折下一根柳枝/拦住,拦住它们——/不能把洗净的云彩叼去/不能把我的蓝天踩碎。
情境历历如在眼前,尤其是末二句逼真的童稚之趣,直叫人忍俊不禁。
又譬如《春二三月》:“细雨濛濛/细雨濛濛/竹笋斜撑江南”。竹笋极小,江南极大。一个极小的事物如何能支撑极大的事物?这就是诗歌的魅力所在,想象的魅力所在。但这种想象又不是毫无依据的。春笋是最能代表生机活力的,我们常用“雨后春笋”形容某事物长势之旺盛。一个最有生机活力的事物当然是支撑江南春天的最佳选择。且是“斜撑”,就愈发显出它的努力,使得春笋和江南的天空构成了一个角度,也构成了一个诗的视角,产生了独特的意趣。
第二个是技艺层面,因多种手法的运用而带来的奇趣。诗人非常善于打破常规思维,逆向掘进,从而带给读者惊喜。有诗评家谓其往往于“平淡中见奇崛”,原因盖也在此。譬如,“鸭子叼着半截发绿的活蹦乱跳的小溪”,“小溪捕捉这小鱼小虾的活泼”,这种“反着来”的语词组合往往给人一种陌生感,一种感观上的冲击,也使诗歌具有了独特的趣味。
其节奏,则往往在看似平缓的叙述中埋伏着一种速度,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一个意外,一个爆点。譬如:
……溪中洁净的卵石浮上沉下/山笋天天向上/青蛙是手机,哇哇叫不停/春天只有山上野兔子尾巴般长/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走向转身的田野/网上买来的种子/半信/半疑(《春天踩着农谚来了》)
末句之妙令人拍案。前面所有平静的叙述和铺陈都是为这末一句的高潮作预设和准备。春天来了,但种子还不敢确信,因为种子本身是“网上买来的”,种子本身的身份就成了问题。尤其说种子对春天的态度半信半疑,毋宁说是怀着新的希望的农人对种子的半信半疑的态度。人与种子之间的彼此疑惑,通过诗人的想象和情感的植入,加上节奏的变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喜剧色彩。
泥土的香味
潘老师一辈子生活在南方,家乡的土地是他诗歌的精神原点。他的诗歌里所有的语词、意象、句子由此生发出来,并不断向云端生长,又扎进大地深处。他与万物对话,化入彼此,在贴近原始脉搏中获得了一种近乎大地之情的古老灵性。这种灵性进入诗歌,便使其有了馥郁的泥土香味。
他笔下的意象都是最生活化的,离土地最近的,是身边的一枝一叶,是头顶的一虫一鸟,是脚下的一沙一石。是极具南方色彩的牛蹄窝窝,是蛙声,是羞涩的桃花,是湿漉漉的草垛,是抖掉了潮湿的梦的谷子……
他写农人在春天的夜里“拉着满车的灯光走向田野/伸手插进竹箩/看看谷种在适宜的温度里/有没有微笑/拉一拉蜷伏着的耕绳/抚摸栏圈里卧着的牛/喂一筐鲜嫩的江南……/春夜很短/短得像枝桃花”(《春夜》)
这活脱脱就是一幅水墨淋漓带着浓浓泥土气息的江南备耕图了。在农人的眼里,谷子发芽像是对会他“微笑”,他又巴不得把鲜嫩的饲料全给牛喂饱,好牵它负轭劳作,为一年的收成作最早的努力。农人急切而满怀希望的心情被描摹得如此细致入微,引人入胜。而末了,“春夜很短,短得像枝桃花”,又是神来之笔,以具象的桃花表意抽象的时间,惜春之情何等真切。
这一切的一切,恐怕又要归功于诗人对生活的深切体验,对这一块土地的真挚热爱了。
诗是生活的一部分。诗更是一种高贵的生活方式。有的时候,越是卑微的姿态,越能显出其高贵来。读潘老师的诗,信然。
- 责任编辑: 邱雯雯 稿源: 宁海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