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李娟感动
- www.nhnews.com.cn 宁海新闻网 2022年09月02日 09:13:1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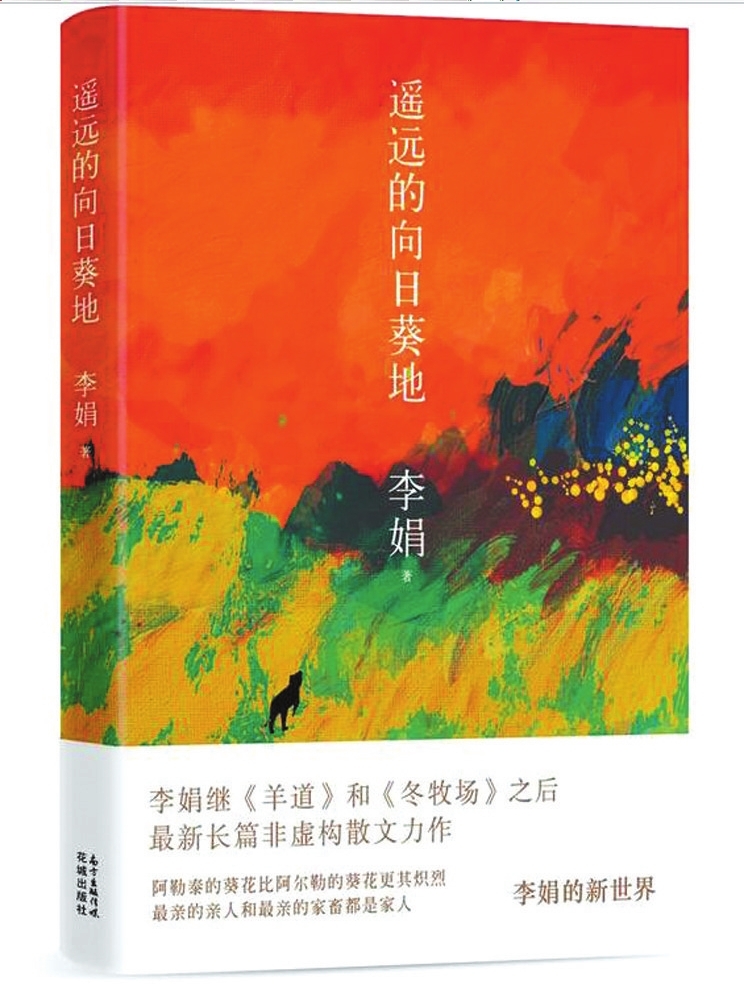
袁聪莲
被李娟感动,因为她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关注李娟,是因为她的文章。那一年,同事们要赛课,抽到一组文章——《我们的裁缝店》《闯祸精》《一个普通人》。我看到了文字,笃定地说:“这不是我们熟知的李娟。那个写《最美是天真》的李娟,文字温婉干净,而且有一定的美术功底。这个李娟,文字充满张力,有一种原始的纯净,有一种悲悯的力量。你看,《我们的裁缝店》里‘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三只鸡和她那因年轻而放肆的美梦。但是我们要鸡干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这几句话,还有《闯祸精》里的‘——似乎到了那会儿,天大的事情也比不上那只可恶的狗重要’……”此后,我知悉,这个李娟用自己的笔,将自己熟知的哈萨克游牧民族的生活状态、民风民俗呈现给读者。
读《遥远的向日葵地》,是因为《九天》。去年,与小伙伴们一起研读《九天》。一篇《九天》,我见着了李娟在荒凉的大地上孤独地行走的姿态:外婆的迷茫与无力,鸡们鸭们狗们的安然与快乐,母亲的梦想与野心,都交织在这块沉睡着种子的粗砾空旷的土地上。明明是沁入血液的苦与痛,却一点儿也不使人压抑,如“等全部家当卸下卡车,太阳已经滑向彩霞簇拥的西方”,这似是一抬头不经意瞥见的灿烂,足以装点这疲惫的大地;“第一天夜里,我们铺开被褥冲着漫天星光睡了一夜”,明明是在“无遮无拦”的冷风中,因为一个“冲”字,多了些豪情。人的力量,人的坚持,人的悲悯,又何尝不是母亲采回的那束“湿润丰盈”了整个春天的野花?
李娟曾经说:“而且我现在仍然觉得,我的散文其实就是一部部标准的小说:有故事的发展,有情节的变化,有丰富的细节,有头有尾。”是的,《遥远的向日葵地》,就是写母亲在阿勒泰戈壁荒漠——乌伦古河南岸承包一片贫瘠的土地种向日葵的两年生活。写妈妈,写外婆,写叔叔,写邻居;写自己家狗与猫,写鸡鸭鹅兔;写永红公社,写阿克哈拉村,写水电站,写那个被用心发现的秘密基地的美景;从搬家写到反复种葵花写到艰难的葵花丰收以及葵花丰收后的艰难。那个赤诚地把自己交给葵花地、骑着摩托车在尘土里风风火火的妈妈,那能够自由穿梭在葵花地的光明与黑暗的漫漫光年中第二天安然归来的洁白的兔子,抑或是一听到“羊”就浑身紧绷、锐利四望的牧羊犬丑丑……所有的一切,就这么鲜活地袒露在我面前,一如这没有任何掩盖的坚硬的戈壁,或者蓬蓬勃勃的向日葵。
诚如作者说,她怀着强烈的渴望,诚实地与人分享那里的一切。读《遥远的向日葵地》,我分明见着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性最为真诚的隐秘世界,那里面有李娟的纯真,李娟的迷茫,李娟的安宁与混乱错杂,还有她的怜悯与李娟式的幽默,更多的是俯拾皆是的漂泊感和孤独,以及无能无力的悲凉。
李娟就那么真诚地袒露自己——
可荒野紧闭,旁边的乌伦古河日夜不息。我赞美得嘶声哑气,也安抚不了心虚与恐慌……
我酝酿出一份巨大的悲哀,却流不出几行眼泪。我全面坦露自己的软弱,捶胸顿足,小丑般无理取闹。可万物充耳不闻。
我无数遍讲述自己的孤独,又诉说千万人的千万种孤独。越讲越尴尬,独自站在地球上,无法收场。
我反反复复地读着这样的一段段短短的话语,心头凝重,继而泪流满面。我们谁又不是“泡沫”般地活着,谁又不是不安宁地处于自己的偏远僻静的戈壁?
“渺小”与“强大”的对峙,给与我的不仅仅是孤独和悲哀,还有诗意与哲思。
李娟笔下的大地是明亮的,生命是明亮的。
即使是“鸭子乱七八糟的闹腾的一阵,在岑静的荒野里,听在耳里是极大的欢欣振奋”;即使是“大风结束时,满世界的尘土,呛得人不住咳嗽”,李娟的记录是——“等尘埃落定,再出门去看,风已转移到天上。河流全部涌向了星空。大风令星空一片混乱,灿烂耀眼。银河流得哗啦作响”;即使是平淡粗糙的日常,做饭时凝视炉火,“久了,身体内部比身体外部还要明亮”,“烙好饼,再烧开一壶水。我压熄火,盖上炉盖,等待回家吃饭的人”。
在永红公社的荒野中,树是单薄安静的人类聚居区唯一的“荣华富贵”;“金色”的白桦树,“它通体耀眼,浑身颤抖,光芒四射”,“一棵树就沦陷了半个秋天”。
而她笔下的“金色”,有了不同的灵魂——
麦田的金色富于深沉的安抚力量;饲草的金色是高处的光明,是皇冠;芦苇的金色最脆弱,最缠绵,最无助,却美得让人窒息;月亮的金色是黑暗的,它最孤独、最自由,与故乡、童年、夜晚有关;蜜蜂的金色最微小,是碎屑,是钥匙;葵花缓升宝座,端坐一切金色的顶端……
读着读着,自己就仿佛是那个穿行于金色与蓝色之中的一尘不染的人,干净而又明亮……
李娟参与母亲的计划,参与劳动,不是沉浸,不是体验,是真实的生活,才能深悟“可大自然无从操控。所有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行为都带有赌博性质。”“种地就是‘靠天吃饭’”“哪怕到现在,我们几乎可以改变一切了,仍无法掌控耕种的命运”。尽管向日葵丰收了,成了黑压压的财富,却榨干了大地的力量,把“母亲和叔叔”榨成了渣,但她的文字始终给与人力量。这力量最大的源泉,在于“母亲”,那个忙碌不息的母亲,坚韧的、乐观的母亲,在强大的不可预知的自然面前,主宰着自己命运又被命运挟裹的母亲,何尝不是一代农民最真实的写照?
我咀嚼着“后记”中的这段话:“这是长久以来我一直渴望书写的东西,关于大地的,关于万物的,关于消失和永不消失的,尤其是关于人的——人的意愿和人的贪心,人的无辜与人的豪情。”《遥远的向日葵地》似是一本母亲的传记,一本戈壁滩上任何一个最后的农民命运延续的传记。
鲁迅文学奖授奖辞这样说:“李娟的散文有一种乐观豁达的游牧精神。《遥远的向日葵地》中,那块令人忧心的年年歉收的田地,不竭地生长着天真的喜悦。她的文字独具性灵,透明而慧黠,边疆生活在她的笔下充满跳荡的生机和诗意。”这种乐观豁达的游牧精神,这“透明而慧黠”,这“跳荡的生机和诗意”,就是母亲。
谁想让自己的文字有感人的力量,就先真正地走进真实的生活。
“在很大程度上。有序的非虚构作品是对一种印象的确认。靠你的诚实呈现力量。”雪莉·艾丽斯说,“当情感被最真实地表现出来的时候,无论这种情感是欣喜若狂,还是愤懑暴怒,文字和语言都会产生一种强大力量。”李娟的文字,就有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召唤我用拙笔,写下这些真实而同样笨拙的文字。
否则,我心神不宁。
- 责任编辑: 林琪 稿源: 宁海新闻网
您当前的位置 : 宁海新闻网 > 文化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