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朴的诗之光自在长明
- www.nhnews.com.cn 宁海新闻网 2022年11月25日 08:59:0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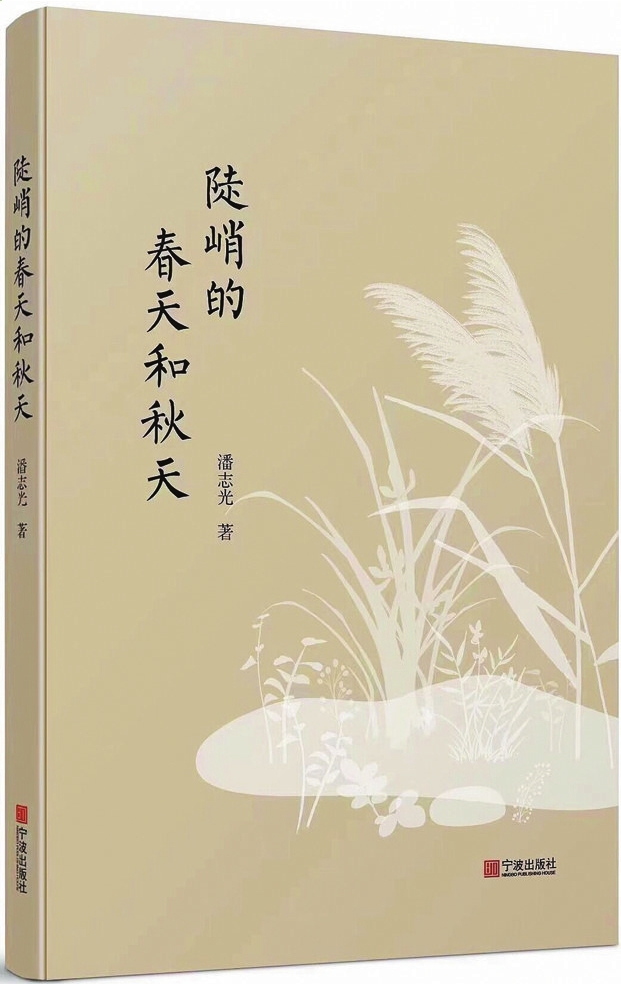
洪迪
潘志光简朴的诗之光自在长明,是当今中国诗坛一帧亮丽风景。
《诗探索》2018年第3辑作品卷《诗坛峰会》栏目发表了《潘志光诗三十首》,并附上诗人创作随笔《跟上队伍》,值得一读。潘志光的处女作发表于1958年。60年代中期便有诗作发表于《解放军文艺》《人民日报》等大报刊。尔后陆续出过《春天像开场锣鼓》《冬天与春天——储吉旺诗传》等诗集。这三十首诗可看作诗人自选的代表作。读它们即是读精彩的潘志光。
其精彩如何呢?让我们先挑出三首来细读。先看《桃子》:
你的目光在桃子上/缠绕了一圈又一圈/你伸手去摘/摘不着桃子//你跳起来去摘/摘不着桃子/你扛来梯子/还是摘不着桃子/拉车上坡的人/胸膛贴着路//有人劝说你捕鱼捉蟹/有人劝说你/种植棉花/种植秋天/你的目光还是在桃子上/缠绕了一圈一圈/又一圈//你拿来斧子/砍倒了桃树
这首诗是够简单的了,石墩子般朴实。有点像童话,又有点像寓言,好像也没有多大多深的意思,用大白话说个不像故事的故事。开头一节,说你想摘桃子,伸手摘不着,平淡,又土。不,偷偷地,有点洋气,将目光具象为可“缠绕”的线。第二节,从摘不着延伸,先跳着试试,再扛来梯子。蓦地来了“拉车上坡的人/胸膛贴着路”,跟上面似乎不搭界,却是极生动地表现摘桃子者的极大努力。这在手法上近乎后现代。第三节,干脆劝说“你”别摘了。不说别干,只说干别的,且将“捕鱼捉蟹”与“种植棉花”“种植秋天”并列,是大扩张,更将“秋天”与“棉花”归于一类。但你的目光之线,还在缠绕着桃子,无休无止。末节更是神来之笔:“你拿来斧子/砍倒了桃树”。桃子终于摘到了,却再也不会有桃子吃了。“你”是谁?摘的什么桃子?
再读《夜色》:
夜色很厚/树走动了几步/又回到原来的位置/我坐下来/听树讲故事/撕一块夜色/做坐垫//夜色有没有薄的地方呢?/出口处在哪里呢?//树走动了几步/又回到原来的位置/我放好双脚/用一颗没有颜色的/心脏行走/双手扶着/弯曲的微风//蟋蟀/用两根触须/捅开夜色的一个窟窿/树,抢先涌了出去
诗中有五个角色:夜色、树、我、微风、蟋蟀。上演着一出活剧。平凡的不平凡。平凡的是故事,不平凡的是角色的活动与动作,因此有一种草根的后现代主义。最出色的是结尾四行。
于是,读《今夜像只陶罐》:
今夜像只陶罐/不是昨夜的那块丝绸/被爆竹烧满了洞洞/严寒和岩石蹲在一起//夜睡着了/偶尔三两声犬吠落在门口//云不动/惟怕夜睡得/像冬眠的青蛙/惟怕夜又延长不醒/老树有没长出新芽?//几点星光/粘在凹凸的夜/半片残月/坠入我泥土般的梦//溪水潺潺/有人在自己身上寻找星星
写夜景,颇别致。全是些常见的字词,要妙在于搭配的方式特别、出奇。这便有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诸如夜与陶罐、与丝绸,严寒与岩石,等等。“惟怕夜又延长不醒”忽然接上“老树有没有长出新芽?”“溪水潺潺”怎么接上“有人在自己身上寻找星星”?这“人”是谁?是夜,还是自己?或者夜与自己合体?夜景体现着潘志光诗的别致。
通观潘志光这三十首诗,可以发现它们自有特色:简朴,自在。这种风格、品格在司空图二十四品中找不到。但它同“空潭泻春”的“洗炼”、“筑屋松下”的“疏野”有几分相近,更疑似于“幽人空山,过雨采苹”的“自然”而有所未逮。且土气过于古气,洋气更胜于土气。故谓之简朴而自在,又沾光于现代、后现代。
通观潘志光这三十首诗,可以发现在诗美创造上自有佳胜之处。首先,几乎每首诗都有自己的诗核、诗眼的发现、发明。比如,《春天像开场锣鼓露出脸儿》,这用作标题的诗句,便是此诗的核或眼,一切皆由此而生发。《外面有人走动》同样如此。《春二三月》的眼或核,则在于“细雨濛濛”、“别怕踩痛春二三月”与“竹笋斜撑江南”。细雨是留下大片前景的好开头,踩痛与斜撑才晶结为诗核。《摆布》的眼正在“摆布”。前面四节八行,将似乎不相干的东西拉在一起,似为杂乱的拼盘,“摆布”一词为一句,妙在点睛,诗便活了,飞起来了。
其次,诗美时空即意境的建构上散放而自在。《外面有人走动》用同题这句开头,紧接着自然是“打开门看一看”。却“没有人影”,便躺下,又听到走动声。如此反复,终于问出“这是谁呢?”诗便自在成了。《牛的行动》起首是“牛蹄/踏碎”,然后由踏而闻,而吞吃,终于“夜的边缘/塌方”。《藤蔓往上爬》全诗便紧紧抓住主体“藤蔓”与其行动“爬”。全诗都是怎么怎么爬。《肉骨头》的诗眼,不在肉骨头,而是在“将肉骨头踢进池塘”。于是便借此写了个诗味盎然的寓言故事,三只狗先是为了肉骨头争得昏天黑地。但当“高个子男人飞起一脚/将肉骨头踢进池塘”,于是便景观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路上走着三只狗/相互间十分亲昵”。诗的本质本体在于创造诗美。美,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中定义为“有意味的形式”,其实它更是有形式的意味。意味才是诗美的灵魂。创造,是发现,更是发明。既是从有中去蔽,更是无中生有。关于三只狗和一块肉骨头的得失之争的寓言,正蕴含着此诗的盎然意味。
再次,诗中多炼出好字眼、好句子。中国新诗界有过好诗的句篇之争。全篇的整体气韵好固然好,有篇更有句实在更好。而多数的好诗往往得益于好句子,而好句子又往往与好字眼密切相关。潘志光诗亦往往深得其助益。《外面有人走动》更让人赏识的是“梨花落着寂寞”、“竹丛摇着半轮山月”、“足迹像鸟儿狭长的叫声/落满厚厚的一层”、“我问梨花和竹丛/山月寂静躲进云层”。《伞》中有更多的好句子,好字眼。有了“缠绕”、“贴在”、“粘住”、“搁在”等等,才有“山路缠绕柴草/太阳贴在我的背脊”“云团粘住鸟儿的翅膀”、“我把伞搁在季节的背后”等好句子。而“我和儿子聊天”这个极平淡的句子,因为跟上两节十二句相抗衡,成点睛,所以特佳。《水中的一棵芦苇》成诗的关键,只在末节:“夜晚,我湿漉漉的梦中/看见一棵挺拔的芦苇/将枝叶伸进了太阳”。这末节的精神尤钟于末句。《藤蔓往上爬》全靠一个“爬”字,全诗十七行,一连用了十个“爬”字。不,“小溪贴着大地流/流过山花和歌声”的两个“流”字,仍在偷偷地爬。
通观这三十首代表作,足见潘志光简朴的诗之光自在长明,足见他厕身当今中国新诗坛,仍不愧为一位有特色的实力诗人。从1958年至今,他的诗龄刚好满满一甲子。照时下的说法,他是一位“40后”诗人,早该靠边,出局了。不,他还挺然站着,还在稳步前行。其中奥秘颇值探索。看来,其着力之处,至少有这样三条:
一曰踏实地。因而富于草根性。他出身乡村,当过兵,蹲过机关,又进了大企业,为兴建企业文化而主编报纸。为人又谦和诚实。他的草根性是两个方面的融合。一方面是熟悉工农民众的生活和习性;另一方面汲取传统文化、古典诗词的丰富营养。
二曰争天时。长期生活的家乡宁海,古属硬气而迂的台州,今归现代大港城市宁波。浙东沿海大得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诗人潘志光写诗虽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却欣然紧跟朦胧诗、后朦胧诗大潮。他的《跟上队伍》说:
写作有点像吃菜,习惯吃某种菜后,在短时间内要改为吃另外一种菜,这对有些人来说很难适应。写作者也有点像运动员,一个原来是扔铅球、掷标枪的要改为举重、打乒乓球,这也会不适应;但再坚持扔铅球、掷标枪,已很难出成绩,甚至有被淘汰的危险。我知道如果原地踏步,诗就会离开我。经过思考,我选择了继续前进,跟上队伍。但继续前进,跟上队伍又谈何容易呢?这就像一个人写字,已经定型了,而要改成写另一种字体,需要花多少的工夫啊!“传统诗”和“现代诗”的感受方式、想象方式、传达方式都不一样。要继续前进,跟上队伍,必须向年龄挑战,跳出原来的写作模式,突破自己。
突破自己,就要学习。因为不学习,就跟不上队伍,就会掉队,就会被淘汰。发扬“钉子”精神,读20世纪早期中国新诗,读波德莱尔、马拉美、瓦雷里,读庞德、勃莱,读希尼、毕肖普,读叶赛宁,读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和巴列霍等,读中国新时期优秀诗人的诗,从中汲取营养。但也注意不全盘西化,力求古今中外的融合。
这是真切的经验之谈。无论青、老诗人,不断克服思维定式、审美定式都不容易。力求融合古今中外,更须有大继承的胸怀与魄力。诗人当有三种年龄:生理年龄、诗写年龄和诗美创造年龄。生理年龄有天然的生、长、壮、病、衰、老。诗写年龄的短长成于客观社会条件与主体意愿。诗美创造年龄,谁都喜欢青春长葆。长葆之术当有六多:多践行,多感受,多思考,多阅读,多写诗,多推敲。多阅读是重营养,实比其它五多更重要,因为它是最紧要有效的推动者。推敲多被自居“天才”诗人所轻忽,要好好向贾岛、何其芳,尤其是特朗斯特罗姆学习。
三曰成特色。诗人不论大小,自成特色,便有立足之地。潘志光之诗是自有特色的。那就是简朴而自在;就是在草根的实地上,尽可能多方汲取中外古今的好东西;就是不论快慢、不论脚印浅深、不论春秋更迭,只顾自在地不辍前行,再前行!
(作者为浙江原台州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著名诗歌评论家、诗人)
- 责任编辑: 林琪 稿源: 宁海新闻网
您当前的位置 : 宁海新闻网 > 文化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