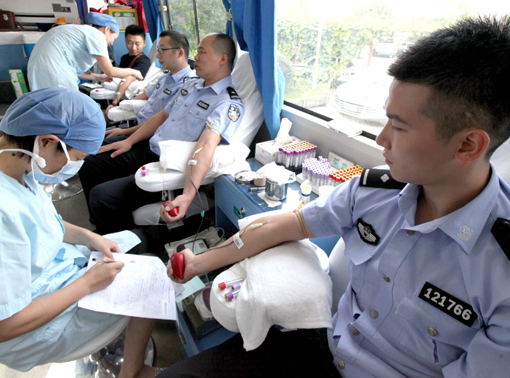| 洗尽铅华见从容 |
| ——品读阿门“者”系列组诗有感 |
| http://www.nhnews.com.cn 宁海新闻网 2014-09-01 09:21 |
(二) 如果把一个诗人的诗路历程看作一条河流,有些东西在变,在不停流动,那么,也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是诗人始终在坚守的。就像河流中的砥柱。 对于阿门,变的是他的诗风,是色彩,是愈见娴熟的技艺——他现在就像是个高明的铁匠,火候怎样把握,怎样使劲,往哪儿使,都胸有成竹,得心应手,信手拈来。 而不变的,是他写作的“姿势”。 有诗评家把诗歌写作分成三种“姿势”,并据此把当今的诗歌写作者归为三类——坚守者、迎合者、推销者:坚守者,他们在寂寞中以虔敬之心面对诗歌,坚持纯正严肃的诗歌写作;迎合者,他们迎合大众的心理和口味,实施“卖点”战略,想方设法吸引读者的目光;推销者,这类人干脆把诗作为生财谋生之道,把诗歌当作商品直接出卖。 阿门无疑属于第一类。他不迎合世俗,更不善自我推销,所以埋头写诗曾经让他的日子捉襟见肘。但他不怨悔,正像他自己所说: 劝自己:简单爱,减法活……/这些年,热闹是别人的事,我偏爱/沉默的事物:灯光,书刊,铅笔,纸页/以及无声的大雪和诗经(《过年者》) 因为甘于“简单”,偏爱“沉默”,所以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诗歌理想。这个理想,在我看来,是一种为诗歌而诗歌,一种对艺术纯粹而执着的追求。尽管,诗人仍这样谦虚:“写来写去还是那首诗/从模仿到重复,我是我作品的抄袭者/虽无罚单/但离优秀,越来越远”(《抄袭者》) 尽管,诗人仍有这样的怅惘:“也许之前的我,类似古代采诗官/只是语词尸体的搬运工?/也许每一个语词都有情人,而我/已找到拯救和同居的秘方?/也许一首诗的完毕,就像我女儿/有了我管不着的命运,甚至不再属于我?/也许我太贪心,想一辈子写诗/并给它足够的宠溺是宿命?/也许多写意味着重复,而超越举步维艰/那就放弃,如同放下一负担、一债务?……”(《写诗者》) 然而,他又马上给了自己这样坚定的回答:“但这样做,我会闲死。十字路口/我选择,做一个喂养语词的诗人”(《写诗者》) 有人说,诗歌写作,天分是不太可靠的。依靠天分写作的诗人,也大抵很难摘取诗歌领域中最高的桂冠。一个有诗歌能力的诗人,才可以渐渐将天分转化为写作持久的可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子将自己最大的敬意献给了但丁、歌德和莎士比亚,而将热情和天分留给了荷尔德林、叶赛宁、兰波。 诗歌能力,显然包含着诸多复杂的要素。写作的持久,也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我以为,这种写作“姿势”的坚持,对诗歌完全出自内心的欲罢不能的热爱,是其中最要紧的。 阿门一直坚定地走在这样的路上。 所以,诗歌带给了他荣誉,诗歌让一位失聪者找到了生活的方向,找到了尊严,找到了一条接通外部世界的特殊渠道,找到了一条通向理想生活和生活理想彼岸的轨道(阿门自己曾说,诗歌于他是“一条必然的自救之路”)。 (三) 如果在这个时代谈论诗歌理想多少让人生疑,或者起码有些矫情,那么,诗人必须要具备写作的诚意,这大抵是毋庸置疑,也是必须的。 读当下诗人的一些诗,有时不免会生出一种疑惑:在诗人和这个诗人创作的作品之间,你该相信谁。诗人?还是诗歌? 这么说,很显然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下不少的诗人和他的诗歌之间是分裂的,不统一的。就像他们分裂的人格。在他们的作品里,你仿佛永远只能看见某种“大”,那种“大”或者“高”压得人喘不过气,叫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 阿门从不避讳自己内心的“小”,他尊重自己内心的情绪,并真实地呈现着自己的情绪,就像:“我中年时,就像中游的水/有些杂质,倾倒月光与目光的少了/多了垃圾、浮躁、污染和虚名”(《治水者》) 就像:“抱恨终天,人前若无其事,人后/丢了魂似的,一颗半死的心/两只悬空的手,三字姓名/被法院或公证处曝光,声名狼藉”(《贪小者》) 正因如此,他有时在诗歌里展示的那种孤独感、无助感甚至于悲剧感,愈加地打动人心: 我的后悔事,细碎、多余/像多年的暗疾,羞于说出/所犯的过失、错误,似浮尘、草屑/因无法阻止。可忽略不计(《后悔者》) 拿月亮当电灯/把沙发坐出一个坑/被睡眠抛弃后,就只能与自己抗争/迟钝,易怒,一不小心就触动生命停止键的开关/之后有大把的时间长眠(《抑郁者》) …… 有诗评家所说,好的诗歌,它应该让人感受到血肉、骨架、呼吸和灵魂。按诗人西川的说法,衡量一首诗的成功与否有四个程度:诗歌向永恒真理靠近的程度;诗歌通过现世界对于另一世界的提示程度;诗歌内部结构、技巧完善的程度;诗歌作为审美对象在读者心中所能引起的快感程度。 虽然,并不是每一首诗都必须要做到这四点,何况所谓的“永恒真理”本身也具有未知性和不确定性,但它至少对广大的诗人们有着一种有益的启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以为阿门很多诗作中对于人生的一些思考和探索,正是符合着这样的定义的。 譬如他对于生命的脆弱和不可预测的感知,从身边亲人朋友的离去,以及到: 从马航失联到韩轮沉没,那么多的人/一下子被海洋,这巨大的坟墓覆盖/仿佛水滴消失在水中,尸骨无存/这让我悲伤,恍惚,麻木……(《去世者》) 在没有空隙的时间之间,生命是一种暂时现象,而死亡就是一种永恒真理。所以诗人最后发出这样的喟叹——“死亡,是一张不漏的网/时间之灰啊/早晚埋我于故土”。 还譬如他从一枚落叶的身上察觉到的“时间的真容”: 隔着窗门,已能清晰看到/落叶的身上,季节的影子——/时间的真容。打扫和清理自己/这一刻,冷,又酸楚地热(《落叶者》) 这些,是否有着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所描述的那样,“像是真理扑动的一角”? |
| 录入: 袁慧敏 责任编辑: 袁慧敏 稿源: 宁海新闻网 |
| 【背景色
|

|
|
|